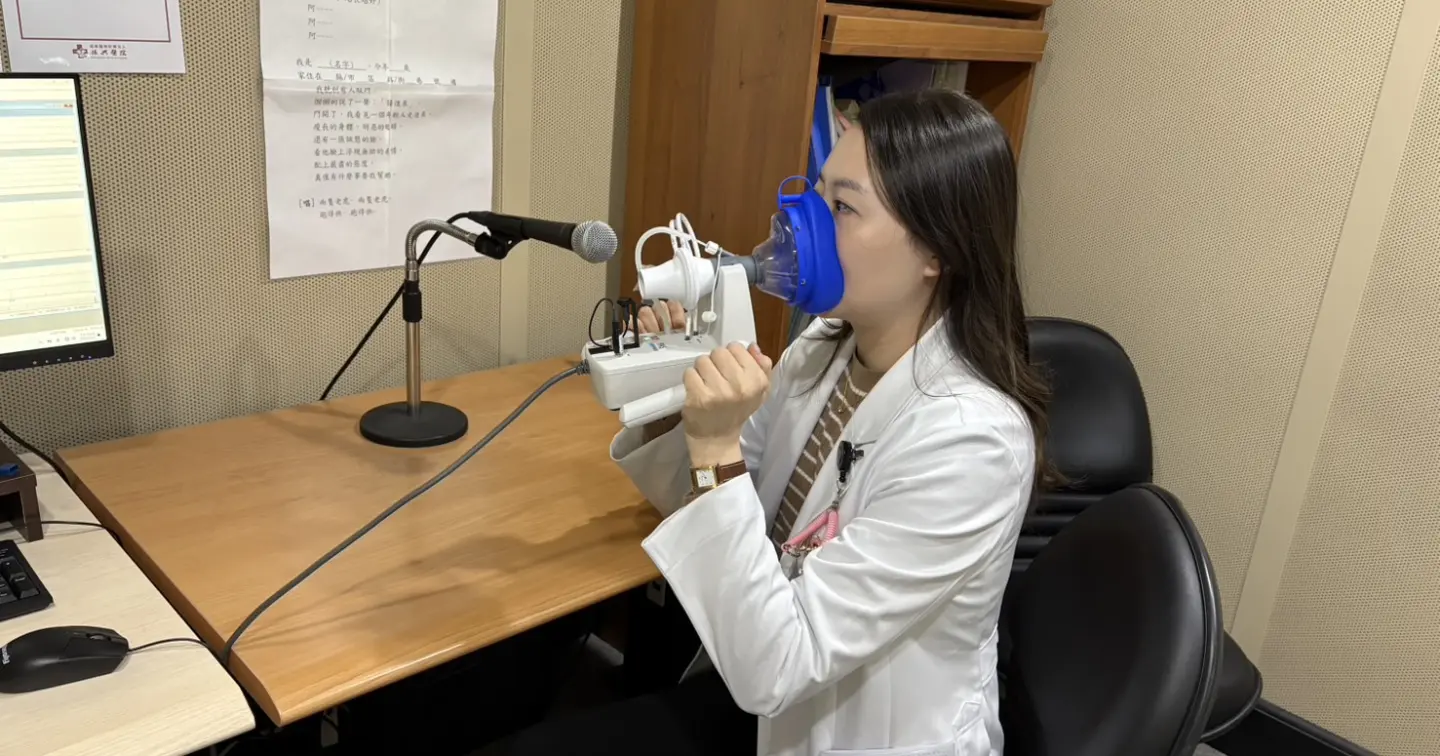長年於摩根士丹利(Morgan Stanley)總部坐鎮的國際金融科技人陳柏翰,毅然從紐約摩天大樓裡辭去高薪工作,轉身回到臺灣,投身一條沒有前人腳印的生技創業之路,而他動心創業的源頭,則來自身邊的摯愛親人──罹癌的父親。
2018 年陳柏翰成立「精拓生技」,一家專攻癌症替身醫療檢測的新創公司,不同於傳統的癌症治療方法,得透過人體直接嘗試不同的癌症藥物,去找到最適合病患的癌症用藥,替身醫療檢測是以血液檢測病患腫瘤細胞進行藥物篩檢,有機會為病人和家屬提供「更精準」的選擇。
從華爾街轉戰生技 沒有預期的轉身
陳柏翰大學主修都市計畫,卻因為在《數位時代》雜誌上看見一則 Red Hat Linux 的廣告,意外踏入資訊科技領域。他當時一口氣上了三遍課,成為台灣最早一批取得 Linux 工程師認證的技術人才。寫程式帶給他極大的成就感,可以從無到有打造出一個真正能運作的系統,這樣的的創造力深深吸引著他。即使英文程度不佳,他仍堅持閱讀原文資料、反覆挑戰英文檢定,歷經無數次失敗後,終於赴美攻讀碩士,並在那裡完成跨領域科技管理的專業訓練。
「人生很多事,是你計畫不了的。」談起投身生技領域的歷程,陳柏翰這麼說。他曾在美國摩根士丹利工作將近 15 年,所屬的部門負責公司核心資訊系統,權限極高,手中掌握的資訊重要到不能自由交易股票,就怕牽一髮而動全身;也曾為了處理系統緊急狀況,值班 30 小時未闔眼,「十秒內沒解決,電話那頭就會不停催趕。」對陳柏翰來說,這份工作雖然高壓但成就感十足,是他職涯的鍛鍊場,直到父親罹癌,讓他的人生重心轉向,也開始思考能為這個世界多做些什麼。
陪父親治療的過程中,陳柏翰感受到的不只是疾病的殘酷,更是資訊的不對等。他觀察到,很多時候對於病人的用藥,都是用了才知道有沒有效,「但病人能有幾次機會?一次一次試,根本太晚了。」陳柏翰聯想到他在金融業寫程式時,系統上線前必須經過嚴密且反覆不斷地測試,「他想為什麼醫療用藥沒有一個測試沙盒,而是需要病人們以身試藥?」每一次的用藥對病患來說都是賭注,但患者通常只有一次機會。

《神力女超人》的對白給了陳柏翰新的想法,成為推動他回臺創業的動力。(圖片來源/陳柏翰)
父親生病那年,他在戲院看了《神力女超人》,其中一句台詞:「If you see something wrong happening in the world, you can either do nothing, or you can do something.(當你看到這世界上發生不對的事,你可以選擇袖手旁觀,也可以選擇挺身而出。)」聽了這一段話,陳柏翰彷彿被雷打中般,「我那時候突然覺得自己應該要做點什麼!」於是他毅然辭去在美國的高薪職位,投入完全陌生的生技醫療,不過他坦言,當時的自己太天真,以為創業就是開公司、申請產品就好,其實過程瑣碎又繁複。
以愛為名的創業 是遺憾而非後悔
回臺創業這幾年,陳柏翰陸續失去了三位至親──父親、外公與外婆。他感嘆地說:「原以為回到臺灣可以多陪親人一些時間,結果反而因為忙於工作,與他們相處的時間比想像中更少。」但他認為這份失落不是後悔,而是遺憾。創業的壓力不只是工作,而是對自己「為了所愛之人創業,卻失去更多陪伴」的反思。
因此,現在的他更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間,也更懂得在工作與生活中找到平衡。陳柏翰每天晚上會陪兒子睡前聊天,「十歲的兒子會問我工作的事,我就慢慢講給他聽。」而兩位女兒在美國長大,英文流利,甚至會幫他練英文簡報,糾正他的發音,他自豪地說:「她們不只支持我,也是我創業過程中的夥伴。」
「生活不只是你能揮出多重的拳,而是就算受到重擊還能繼續前行!」陳柏翰用這段話形容他的創業哲學,也是他的生活態度,無論是輸掉比賽,或是募資失利都沒關係,關鍵永遠是跌倒後能不能再站起來,重新出發。
替身醫療:為病人爭取選擇權
精拓生技專注的「替身醫療」是一種替代病患本人進行藥物測試的方法。透過血液中的循環腫瘤細胞(CTCs)培養出病人特有的癌細胞,再與多種藥物進行平行反應實驗,協助醫師與家屬做出決策。
陳柏翰強調,「這不是治療,而是幫助你做決定的資訊,你可以把它當作癌症用藥的 Google Map。」病人與家屬常要面對健保與自費、價格與副作用等各種兩難抉擇,「如果我們可以給出多一點資訊,病患就有機會活得更有尊嚴、有選擇。」精拓生技利用替身醫療,提供病患和醫師更多參考依據,為病人爭取到多一些的掌握權。
他進一步解釋,其實在醫學上癌症並沒有「治癒」這回事,只有「是否控制的好」。他說,其實大部分的人體中都可能存在癌細胞,只是尚未發展為癌症。而精拓所做的,是盡量讓醫師與病患知道「哪些藥可能有用、哪些需要避開」,將風險降到最低。
學歷不是重點 解決問題才是關鍵

精拓生技於「2024 新世代癌症治療論壇論壇」分享癌症新知(圖片來源/陳柏翰)
令人驚訝的是,這樣一間還在發展中的生技公司,去年招聘實習生時收到了超過 800 份申請,最後僅錄取七位,錄取率僅有 0.86%,甚至比擠進哈佛大學還困難。
不過陳柏翰強調,「我們的實習生不是來打雜,是來做專案的!」他舉例,其中一位高中生對生物與 3D 列印有興趣,從頭自學,成功完成專案並取得兩項專利。對陳柏翰來說,精拓生技看重的並非資歷與學歷,而是思考與執行力。
他也堅持,精拓生技的夥伴要接受跨領域的訓練,除了經常邀請醫師來演講,也曾找來擅長敘事的導演、探討情緒的催眠師,或者分享募資經驗的創投等,因為他始終相信,未來絕對是需要跨領域、會解決問題的人,而非只會死讀書的人。
更重要的是,精拓生技不忘初衷,默默進行著許多「非正規」卻充滿溫度的行動。五年前,團隊聽見馬偕醫院的醫師提起,有些家長不忍孩子承受化療之苦選擇放棄治療。這讓陳柏翰心生不捨,隨即啟動「Little Star」兒童癌症計畫,為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免費檢測服務,並意外發現自家技術能成功培養出腦癌細胞,突破過去醫界極難跨越的技術瓶頸。
他們相信,科研也能有溫度。精拓每年不辦傳統尾牙,而是舉辦「電影欣賞會」,邀請癌友與醫師一同參與,讓彼此在輕鬆的氛圍中交流生命經驗,留下笑聲與陪伴。此外,團隊也多次參與國內外的展覽與競賽,抱著嘗試的心情報名美國矽谷實境募資節目《Meet The Drapers》,沒想到一路過關斬將,最終拿下總冠軍,獲得國際投資人的青睞,也讓精拓正式邁向國際,成功轉為美國公司。
整合 AI 與數據 讓精準醫療真正落地
AI 的崛起,正在重塑每一個產業的運作方式,生技醫療也不例外。陳柏翰深知,資訊的整合與技術的進化,將是未來精準醫療能否真正落地的關鍵。因此,他不只是談理想,更身體力行地在精拓生技的實驗室裡推動數位轉型。
目前,精拓生技已完成實驗紀錄的全面電子化,將傳統以紙本記錄為主的流程,轉為即時資料輸入與系統管理。起初確實也受到一些阻力,但他知道,這是生技業未來一定要走的方向。
然而,電子化只是第一步,接下來的重點,是自動化與 AI 模型的導入。精拓生技正嘗試將細胞藥物反應的實驗數據,及基因檢測與臨床資料做整合,進一步透過人工智慧進行橫向分析與預測,幫助醫師在時間有限、資訊破碎的條件下,找到最有可能有效的治療選擇。
陳柏翰相信,未來的實驗室,應該能讓人類脫離重複性操作,把時間還給判斷、創新與陪伴病人的那一端,「這不是幻想,是我們正在努力實現的藍圖。」
爭取多一點時間 也許能再擁抱一次

精拓生技創業艱辛,卻也在路上獲得許多國際獎項的肯定。(圖片來源/陳柏翰)
創業從來不是百米衝刺,而是一段漫長的馬拉松,對陳柏翰來說,他的初心不是為了賣公司、賺大錢,而是希望這個世界能擁有多一點可能。精拓生技致力於投資在自動化、資訊化的建置,努力降低成本,讓替身醫療檢測能更普及、更平價,因為他深知,若這項檢測若是過於昂貴,很多家庭就失去了選擇。
精拓生技或許不是醫療奇蹟的代名詞,卻是許多病人與家屬陷入茫然無助狀況時的一盞指路明燈。這些年來,精拓團隊走進過無數的家庭,他們與病人站在同一陣線,從陌生到信任,甚至成為朋友,也曾經歷過病人因為延長生命,而有機會與疏遠的家人和解。
陳柏翰感性地說:「我們做的,也許只是幫他們爭取這麼一點時間,但這一點點,也許就足以讓一個家庭能夠好好說再見。」陳柏翰這場從金融業跨足生技領域的創業旅程,從來就不是為了成為英雄,而是為了讓這個世界,多一點溫柔,少一點磨難。